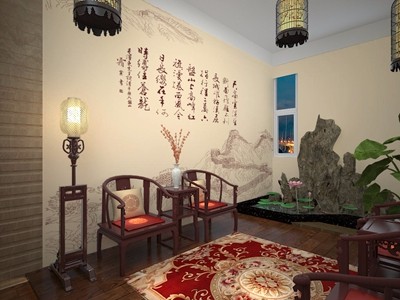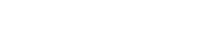青少年饮酒行为同伴影响力的性别地位差异
和上一期情侣和情侣朋友圈对个人饮酒的影响(Kreager and Haynie 2011)一样,青少年处于行为模式定型阶段,较容易受到同辈的行为影响。然而我们不能孤立地看行为影响,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影响别人的。人的行为内嵌于社会结构中的,受到社会结构中规范、文化、身份的约束,因此,我们是否习得别人的行为、多大可能受到影响,也会被自己和对方所自带的规范、文化、身份约束。比如,下级肯定是容易被上级的喜好影响的,而不是相反;少数族裔也较容易是被主流人群影响;女性也或许习惯迁就男(也可能相反),并认为这在文化上是理所应当的。
既往解释青少年饮酒行为传播的理论主要为同伴影响力模型和情景背景模型,前者基于Lazarsfeld、Merton、McPherson等的趋同理论(homophily theory),后者则包括影响个人行为模式的情景和背景因素。趋同理论认为之所以我们会观察到朋友之间的行为有相似性,是因为本来同样类型的人们就容易聚集在一起。今天的推文是Arizona State的Monica Gaughan发表于JHSB比较经典的一个对饮酒的研究,运用地位特征理论(status characteristic theory),考虑地位差异代表不同的同伴影响力,并强调,不论是趋同还是行为影响,都受到先赋地位的制约。该研究着眼于性别为代表的地位特征差异,基于全国青少年健康追踪调查(Add Health)的知己组合(best friendship dyad)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加以检验。
地位特征模型假定先赋地位(ascribed status)形塑行动的互动模式,性别就是一种先赋地位,而在普遍的父权制之下,男性的文化地位和社会规范赋予的地位都高于女性,男性可能对应更高的同伴影响力。检验结果显示同性的知己组合在饮酒频率上相互影响,但不同性别的知己组合则有不同的同伴影响力:男性知己可以影响女性的饮酒频率,但女性知己不能影响男性。
本文的贡献在于使用知己组合成对数据验证了同伴影响力的性别结构差异,这种差异不宜再被忽略。
同伴影响力模型基于趋同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认为饮酒行为在酒肉朋友内部趋同,新加入的朋友早晚染上酒精;同时,社会控制理论则认为与家庭、宗族宗教、教育机构等传统组织的链接,可以缓解同伴影响力模型。如,良好的家庭关系可以让父母有效管束子女的不良行为,个人的宗教管束、良好的学业、积极的校园活动参与都有效避免来自同辈朋友的影响,从而避免或推迟饮酒。因此,如图1,自身和同伴的家庭、宗教、学校等背景都要加入模型。
本文的核心问题便是知己组合的性别结构如何作用于同伴影响模型,检验方法是分性别知己组合的子样本模型,这是本文有趣的地方。关于自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受到条件变量的作用,一般的回归方法会加入自变量和条件变量的交互项做调节效应处理。但是,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要求样本之间的独立性,即朋友之间相互独立,于是样本成了无互动关系的“绞肉机”(Freeman 2004)。可是由于趋同(homophily),事实上朋友这个二人组之间的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交互作用的误差会被人为的缩小。因此,本文的特点在于利用成对数据,如图1,因变量个人醉酒频率(Adolescent Nominator Drunkenness)和朋友醉酒频率(Friend Drunkenness)之间相互影响。图1可以用以下公式表达
Y1和Y2分别是受访青年本人和被点名的知己的醉酒频率,本文的关键就是估算Y1和Y2之间的相互影响,即B12和B21这两个系数的关系。下标首个数字表示被影响者,第二个数字表示施加影响者,故B12表示知己醉酒频率对于受访青年醉酒频率的影响。X1k便是受访者本人的背景变量,包括家庭关系(family closeness)、宗教虔诚度(religiosity)、校园问题(School Problems)和校园活动参与度(School Alienation)。X2k则是被点名的知己的背景变量,同样包括上述4个变量。
Kreager和Haynie (2011)在关于情侣及其交际网络对于个人饮酒的研究中使用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dependence Model),同样适用成对数据,同样考虑到双方背景特征对于因变量的影响,但假定双方因变量之间无关。而本文将知己双方饮酒频率作为各自的因变量,又互为对方的解释变量,形成路径分析的非速归模型。孰优孰劣,依语境而定,Monica Gaughan的处理方法,使得系数递归,如果样本量足够并且模型identified可以拟合的情况下,用于横断面数据是很有益的。
数据来自全国青年健康追踪调查(Add Health),详细描述可参照上一期。因变量醉酒频率是0-7的序次得分变量,男生平均得分1.18,显著高于女生。主要的控制变量为传统主义(Conventionality)、家庭关系和人口学特征。传统主义包括宗教虔诚度、校内参与程度、校园问题等,以控制宗教影响、积极的校园活动参与对于酒精传播的抑制作用。本文还控制了研究设计的影响,加入全员入样(saturated)和核心的全国代表样本(core)的二分变量,另外在回归结果中加入了双方互认(reciprocated)的二分变量。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基于地位特征理论,不平等的性别地位会否作用于青少年饮酒的同伴影响力模型。要回应这个问题,就需要关注两点:同伴影响力和受同伴影响力的性别差异,需要关注男生醉酒频率和背景特征对女生醉酒频率、女生醉酒频率和背景特征对男生醉酒频率的回归系数。
表2显示了饮酒行为的同伴影响模型结果。考虑了知己组合的性别结构,故有4对知己组合(2x2):女-女、男-男、女-男、男-女。要回应本文核心问题,需重点关注最后两栏结果。
影响力方面,男生大于女生。第4栏“女生点名男生为知己”模型中,有471位女生的知己是男生,女生个人对男知己频率负向非显著,但男知己对女生醉酒频率的影响系数正向显著(0.35),男知己醉酒频率每提高1个单位,女生本人醉酒频率也相应提高0.35个单位。在知己背景特征中,男性知己在校问题程度系数(0.11)和年龄系数正向显著(0.43),说明男知己在校问题每提高1个单位,或每年长1岁,分别提高女生本人0.11和0.43个单位的醉酒频率,男知己对女生本人的“入坑”能力不弱。第5栏“男生点名女生为知己”模型中,有558位男生的知己是女生,但红颜知己的影响力不明显,反而受到男生本人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38。女知己的背景特征仅有宗教虔诚度显著(-0.05),选择虔诚女生为知己的男生醉酒频率显著较低②。加上第3栏中男生对基友醉酒频率有显著影响(0.77),可以认为性别地位对同伴影响力的不平等作用相当明显,男生更容易影响同伴,而女生则不然。
②这个系数存在选择性误差:选择有虔诚信仰女生为知己的男生自身更可能有信仰,也有可能是交往当中女生突然转向宗教而改变男生饮酒行为(编者注)。
受影响力方面,女生大于男生。第1栏和第2栏分别是“女生点名女生为知己”(下称闺蜜)和“男生点名男生为知己”(下称基友)的同性知己模型,可以看出受影响力的性别差异。虽然女生本人受闺蜜影响(0.41)小于男生本人受基友影响(0.52),但女生仍然受到大部分闺蜜背景变量的显著影响,但男生没有受到基友背景变量的显著影响。加上第4栏男知己对女生本人醉酒频率的显著影响(0.35)和第5栏女知己对男生本人醉酒频率无显著影响,可以认为性别地位对同伴影响力的不平等作用相当明显,女生更容易受到同伴影响,而男生则不然。
结果显示了影响力和受影响力的性别差异,反映的是男女性别地位造成影响力的差异,地位较高的男生影响力较强,同时受影响力较弱,在同伴交往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女生则反之,处于被动地位。文章虽然关注性别影响力的差异,但实际关注其幕后元凶——性别地位差异。这就邀请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男性对女性好友、知己的影响强烈,但女性对男性的行为影响则很弱?这里基本可以排除趋同homophily的作用的,因为双方都同样处在一个二人组中,但给对方产生的影响却不同。是性别规范导致的期望、约束力不同,还是男性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不自觉地习得了不同的外显行为模式,导致男性更容易将自己的人格、性格、行为倾向用外化的方式传导给外部环境和他人?这是否有利于解释男性的外化精神疾病(如物质滥用、情绪障碍)更多,而女性的内化精神疾病(如焦虑抑郁障碍)更多?
当然,本文存在一个层次问题:本文只利用个体一层数据,但知己组合和学校都是分层次变量,个人醉酒频率可能聚类于此,如上一期情侣及其朋友圈对个人饮酒研究中就加入情侣层和学校层变量。考虑到成文于2006年,本文使用成对数据研究同伴影响力,也是相当前卫的。
作者 梁声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博士研究生);杨晓照(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热门文章排行
- 立遗嘱前必读!中华遗嘱库揭秘五大常见问题
- 预算绩效评价业务审计常见问题及建议
- 原创丨金属疲劳基础 : 应力-寿命设计法
- 新闻动态 智联视界重塑未来!Crestr
- 三江源头玉树州完成退化草原修复超770万
- 欧维姆:技术创新助力“天眼”灵眸察秋毫
- 青少年饮酒行为同伴影响力的性别地位差异
- 产业洞察-产业资讯_ 最新动态_前瞻财经
- 苏州唯创特取得太阳轮齿面检测装置专利能够
- 碳化硅晶圆片划片切割方法
最新资讯文章
- 欧维姆:技术创新助力“天眼”灵眸察秋毫
- 原创丨金属疲劳基础 : 应力-寿命设计法
- 摩根大通:2024年HBM TCB键合机
- 中国钢结构协会
- 原创丨金属疲劳基础 之三 应力-寿命st
- 金属重构未来:人形机器人竞技与科技巨头的
- 时代地智申请基于周次累积钻具疲劳预测方法
- 基于Y-GAMA的河南某变电站项目结构选
- 2024十大气候变化科学新见解 One
-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17年度广
- 2025年中国钢化玻璃市场需求、竞争格局
- 小12箩利洗澡视频 MBA智库
- 果冻入口3秒自动进入V
- 2025油价调整窗口时间表汽油价格多久调
- 腐蚀身边的破坏者
- LMH盐水缓蚀剂为您的系统打造专属“防腐
- 欧精品美高清砖码
- 关于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问题解答
- 2025年4月轿车销量排行榜!吉利星愿成
- 碳化硅晶圆片划片切割方法